我突破了国际上生物脱氮研究领域120余年无法逾越的难题,让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应用于城市污水、炼油废水、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等领域的污水治理工程。正是微生物催生了奇妙的反应,中华民族的祖先酿造了美酒琼浆,古埃及人做出了美味的面包。而我,则从中破解了水污染的治理密码。9月3日,在2019年度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从贵州省委孙志刚手中接过了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从台下走上颁奖台,只有几米之遥,但我的科研之路,却整整走了20多年。我就是周少奇,贵州科学院副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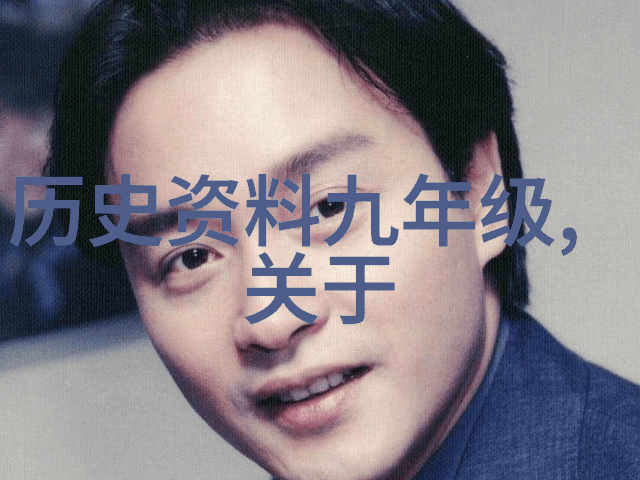
“跨界”科研让我灵光一闪。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晚年提及创新人才培养时,他回忆起自己年少时既学理科又学绘画和音乐的情况,他认为艺术上的修养对他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这开拓了他的科学创新思维。这就是“跨界”的妙处,对此我深有体会。我作为理工男,从中学时代就对哲学、历史比较感兴趣。在本科到博士后期间,我横跨化工机械、工程力学、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工等几个大专业,成为我国发酵工程学科培养的一位博士后。
之后,我将研究方向锁定在环境工程上。1996年,我到香港大学从事环境生物技术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在导师方汉平教授指导下,从未涉足过环境专业的人类,一边看教材,一边做实验,不久就入门。当今世界,无论是在城市化进程还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环境问题。在这场面临挑战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这时候,“跨学科研究”让我灵光一闪。

只要环境适当,一种细菌在昼夜间可以繁殖出数十亿个。一切生命都需要消耗营养物质,而微生物也不例外。如果能从微生物中找到氮磷克星,那么一切便迎刃而解。这是我坚信的事实,将之前所学的生物技术应用到环境工程上,一定会找到一个突破口。
翻越一座百年的科技高峰 我们的大脑总是追求更高层次的问题解决方案,我们试图通过创新的方法来改变现状。但最终,它们往往被限制在理论框架内,因为它们并没有真正地触及实际问题或需求。不过,就像经典物理一样,最伟大的发现往往来自于这些尝试超越传统观念去寻找答案。

经过1000多个日夜实验和分析,我率先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理论——电子计量法。此后10年间,我不断研究与摸索,相继获得了一系列电子计量方程与系统计量模型,为环保治理提供理论基础。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不过即便到了拿工资倒贴进行调查仍不放弃,也没有一丝退缩的心情。我们也得知很多人并不理解我们的努力,他们甚至觉得我们的工作毫无价值。但我们知道,没有那些反对的声音,我们今天取得成果也不会这么快出现。

2002年,当选派到贵州省环保局挂职任助理局长时,当时的一个重大任务是推动城市污水处理建设。当时,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传统处理方式,比如化学药剂辅助处理,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却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我带领团队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案并成功实施,使得整个行业都发生了变化,为国家节约巨额资金同时减轻排放压力,同时还提高了生活质量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环保事业再次重燃希望之火!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故事需要讲述,比如威宁草海这样的地方保护项目,以及西部农村地区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改善生活条件等。但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哪里还是何种形式,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用心,用智慧,用爱心去探索每一个角落,每一次挑战,那么未来一定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