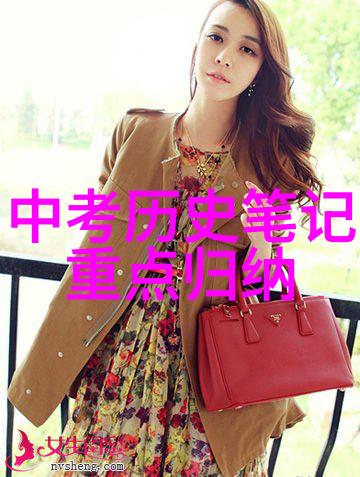如果你想了解玉,且安静地做自己,并且肤发的温润、关节的玲珑、眼目的光澈、意志的凝聚、言笑的晴朗中去认识玉吧!(作者:张晓风,中国著名散文家)

只是美丽起来的石头
一向不喜欢宝石——最近却悄悄地喜欢了玉。宝石是西方的产物,一块钻石,割成几千几百个“切面”,光线就从那里面激射而出,势凌厉,美得几乎具有侵略性,使我不由得不提防起来。我知道自己无法跟它的凶悍逼人相埒,不过至少可以决定“我不喜欢它”。让它在英女王的皇冠上闪烁,让它在展览会上伴以投射灯和响尾蛇(防盗用)展出,我不喜欢,总可以吧! 玉不同,玉是温柔的,早期的字书解释玉,也只说:“玉,是石之美者。”原来玉也只是石,是许多混沌生命中忽然脱颖而出的那一点灵光。

克拉之外
钻石像谋职,把学历经历乃至成绩单上的分数一一开列出来,以便叙位核薪。玉则像爱情,一女子能赢得多少爱情完全视对方为她着迷程度,其间并没有太多法则可循。以撒辛格(诺贝尔奖得主)说:“文学像女人,你为什么喜欢她以及为什么不喜欢她的原因,她自己也不知道。”其实,有客观标准,它们硬度昌莹、柔润、缜密和刻工都可以讨论,只是在最后关头,却只剩下“喜欢”两字,而这正如买卖,不是克拉计价,而是我珍重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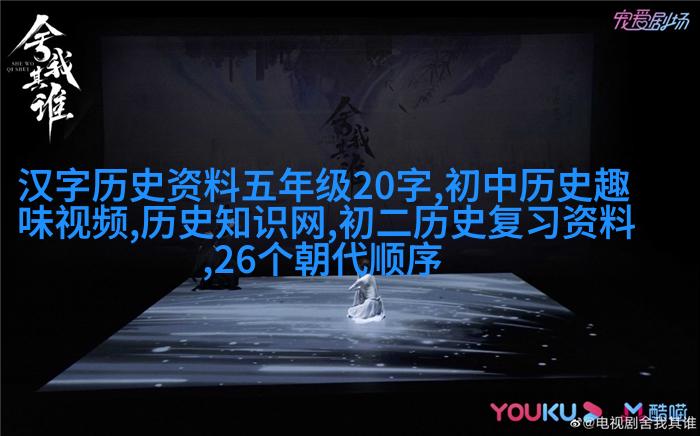
不须镶嵌
钻石不能佩戴,只有经过镶嵌,那才显得完满。而玉呢?虽然也可以镶嵌,不过却显得有些多余,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直接做成戒指或簪笄。这一点沉实比金属性冷冷硬硬的地砖要好吧? 不佩戴的是好的,它们既可把玩,又可做小器具,可以象征富贵吉祥,如意,或用以祀天,还能示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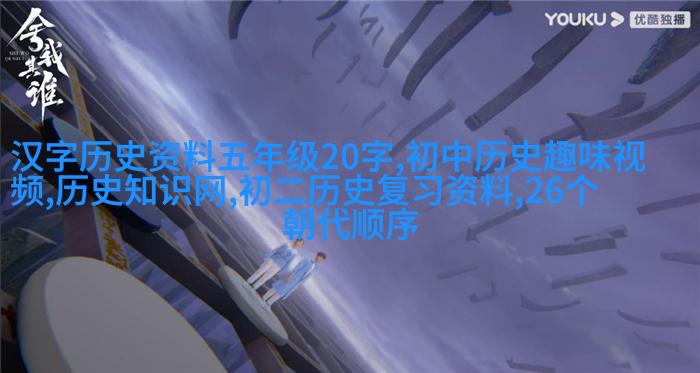
生死以之
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全世界跟他一起活——但一个人死的时候,却谁来陪他一起死呢? 中古世纪有出质朴简直的大剧叫《人人》(EveryMan),死神找到那位名叫人的主角,说他的时间已至,但不能宽贷,只准他结伴同行。人人找“美貌”,“美貌”都不肯跟他去;人人找“知识”,知识也不愿意到墓穴里去相陪;人人找“亲情”,亲情也不顾……世间万物,只有人类在死亡时需要陪葬品吧?

玉肆
我在一个专门售卖高级珠宝的地方走进,在这里看到了一块看似蛀木又像土块的一样东西,我仿佛看到了一张枯涩凝止悲容。我驻足良久,对店员问道:“这是什么样的材料?多少钱?”店员回答说“你懂不知道?”我回答说,“并不懂”。店员笑了笑,说:“那就不要问!”我应该生气或者辩论,但这次选择了微笑离开,因为我更讨厌争辩,即使痛恨学校里的那种形式化无聊的情形。在这个世界里识货的人又有几个呢?
瑕疵付款时,小贩又重复了一次:“这玛瑙再便宜不过了。”然后加上一句,“真的,不过这么便宜也有个缘故,你猜是什么?”我轻声回应,“因为它有斑点。”小贩惊讶地说,“哎呀,看来你真的看出来了,这串项链如果没有瑕疵,那价格就不得了啦!”
然而,当这些话语穿越岁月,每一次心灵对此事深思熟虑后,我发现其实对于那些斑点瑕疵的小瑙子,我们是否还能心存侠气,为何要将它们排除于生活之外呢?水晶中不是有一种叫作"发晶" 的种类吗?虎有纹豹有斑,有谁嫌弃过它们纯色的毛皮啊?
当我们站在历史长河中的某个节点,无声地审视着那些曾经被抛弃,被遗忘的小瑙子,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到每一种存在,都值得尊重与珍惜,就算它们表面的明亮被一些细微的问题所打破。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理解,那么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更加丰富,更添几分诗意与哲理。不仅如此,这些瑕疵反而成为它们独特魅力的源泉,让我们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内在价值,而非外表完善。
所以,当下一次遇见这样的场景时,如果有人问起我的态度,我想告诉他们:即使是一枚普通琐碎的事物,如果你的眼中能够看见其背后的故事,无限可能性,以及人类对美好事物追求与欣赏的话,那么,即使最简单的事情,也可能变成生命中的独特礼物。但记住,最重要的是,不必急于评判别人或自卑于自己的缺陷,而应当学会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无论其如何看待自己的定位,都应该勇敢前行,用真诚和智慧去感受这一切。你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