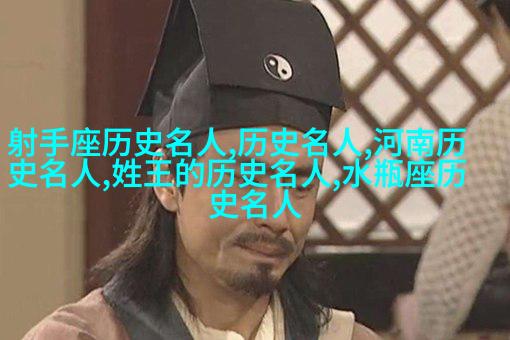在深入研究西方文艺复兴和晚明社会文化时,我们发现两者虽在规模、广度和深度上存在差异,但却共享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尘世生活中个人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个性的解放。然而,文艺复兴还强调了理性与科学的重要性,并且鼓励知识的获取,认为人的价值和潜能是无限可塑,而人类可以创造一切。相比之下,晚明社会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为思想武器,对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其追求的是自身享乐而忽略了责任感和自我价值追求,这实际上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及颓废生活方式。

弗洛姆指出,“人的本质、情欲和忧虑都是文化产物”,而伯纳德则认为“高等动物尤其是人方面,本能即使不是消失,也是在退化”。因此,如果禁欲主义被视为对人性的异化,那么晚明社会所倡导的人生观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性扭曲,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张扬。这种缺乏主体意识层面的自我审视,不仅没有促进真正建设性的发展,也缺乏长久存在的合理基础。
任何一种思想或行为都紧密相连于当时社会现实,它们代表着倡导者的主观思考以及对现实世界理解。社会现实是思想萌生的土壤。在面临巨大经济发展并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情况下,商品经济带来了丰富物质生活,同时也引发了一股奢侈享乐风潮。而金钱在新环境中的作用迅速膨胀,使得官员们利用特权参与商业活动,从而造成了官与贾无别矣的情形。

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主要体现在程朱理学中,它作为明代官方思想被严格确定下来。这一体系以束缚人性、压制人欲为特征,在贫乏物质生活和严厉控制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下得以维持。但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丰富,以及政府无力挽救危机,王守仁提出了良知学,以内化传统道德规范试图重建其权威。他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等命题,以期通过内心自然的情感来弥补传统道德缺陷。
李贽更进一步,他走到了时代前沿,用最激烈的话语挑战传统。他不仅接受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事务,而且认为这都是自然趋向,无需他人的教导。他把势利之心看作人类本性的必然,是无法避免的事,因此应该接受这一点,并将其作为整个道德体系的一部分。他推崇人人顺其自然地去做,没有拘束,没有强制,只要人人满足,就会有太平安定的社会。这一思想虽然冲击了旧有的伦理标准,但也反映出他对于当时普遍趋势以及人类本能的一个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