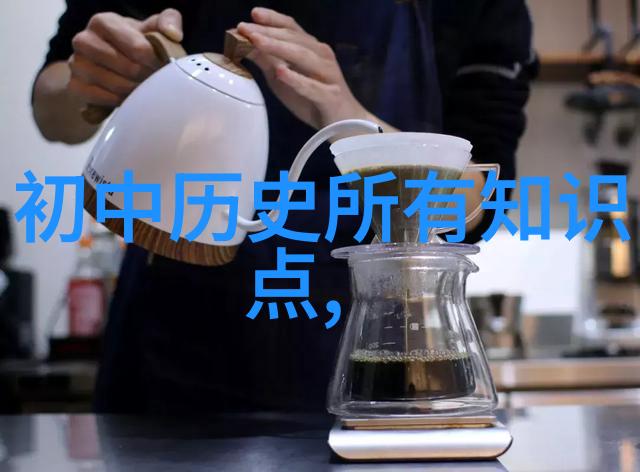美国人对欧洲的“鄙视”文化观念的反击,始于开国先辈,他们逐渐形成了与欧洲有所区别的传统,并从被动的防守转向主动的进攻。在美国独立前后,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新思想和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君主制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启蒙时代的人们很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大洋彼岸看作是由未开化人居住的地方,以证明科学理性的胜利。

在这一时期,“美洲退化论”的影响最为深远,它并非源于启蒙时代,而是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重要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布丰等人的作品中,如《自然史》。布丰认为美洲动物和印第安人都存在退化,在他的眼中,美洲环境导致生物种类减少、力量下降及外观失去魅力。而其他学者如科内利乌斯·德波和纪尧姆-托马·雷纳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将其推向极端,对新世界进行全面否定。
然而,当这些观点遇到来自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宣告独立,并最终赢得独立战争胜利的事实时,一些开国先辈开始积极回应这种偏见。他们认识到这种论调不仅侮辱了自己国家,而且损害了人类文明进程,因此决定进行反驳。

詹姆斯·赛瑟尔认为,“美洲退化论”的两大内容是:第一,美洲动物种类较少、力量不足、外表也不及欧洲;第二,从旧世界迁至新世界任何物品都会变得发育不良且失去活力。一旦欧元踏入美土,他们便开始衰落。约翰·布利斯特德则总结称:“在某些东西(即气候)中,有一些东西必然削弱所有生活其中动物体质和智力的能力,不管是人还是兽都是如此。”
这些观点虽然被部分学者接受,但也遭到了批评。当法国博物学家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德・布丰系统阐述其关于自然史的时候,他确保移民后裔不会发生退化,只要他们能改变新环境,使之从荒凉变成宜居之地。然而,这样的理论并没有指向移民后裔,而是构建了一套科学依据来支持对美州印第安人的退化论,其影响广泛,让许多人相信“气候”会让生物变得低劣。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朝退化”命题不断完善,并由多位学者进一步阐释,如荷兰哲学家科内利乌斯・德波和法国学者纪尧姆-托马・雷纳尔。但尽管这样的理论受到了一定的重视,却无法逃脱事实检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留下的影响仍然存在,为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此事件不仅展现了美国对于自身文化优越感,也展示出开放性与挑战性,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何通过知识与信仰之间紧张关系来理解过去,以及它如何塑造我们的现代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