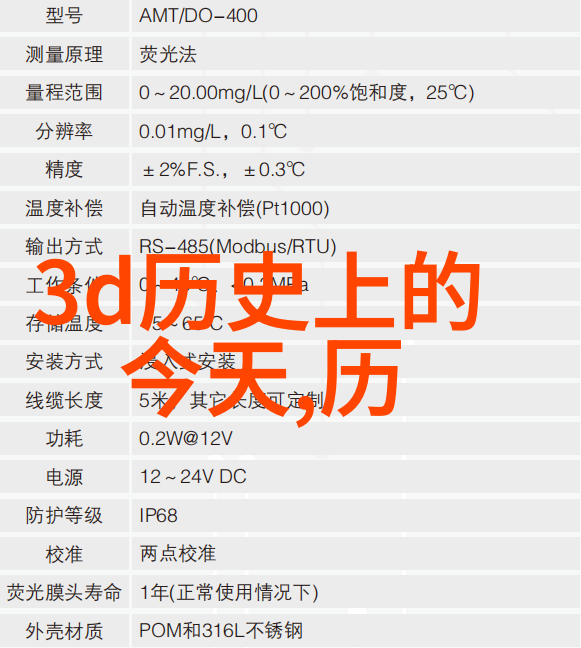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天地、万物以及以礼仪为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诚者,天之道也”,“诚”即是“天道”,只要能够扩展出这份德性的本质,就会达到整个宇宙间所有事物的一致。
孟子更以简练的话语概括了“心学”的思想:只需将心中的善良发挥到极点,便可知晓自己的本真,也便可知晓那超越于一切事务而不变动的心灵原理(《孟子・尽心》)。这里,“心”指的是人的内在深处,那种纯洁无瑕的情感,是我们固有的仁义礼智根基。在这里,只要我们用全力去关怀他人的福祉,便可认识到自己真正应有的形态;而当我们明白了这种自我的本质时,我们就明白了宇宙间最终追求的是什么——一种平衡和谐状态。

先秦道家的思想同样强调着这种精神实体之间存在的一致性的概念。老子的哲学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来源于一个不可见不可闻但却存在于一切事务中的根本力量,这就是他所说的那个永恒不变的事实或法则—道。在他的看来,人们应该顺应自然,不抗拒变化,因为变化正是生命力的表现。他写道:“道生了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并且接着说道:“故曰:得通神,以至明.”(《老子》第25章)
庄子的哲学更进一步,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他把人类放置到了宇宙大舞台上的位置,并且提出人类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一切生命共同参与进来的部分。他说:“我乃世外游侠,与草木为伍,与山川相随,与日月共行。”

西汉武帝时期,由于需要加强国家权威,加快朝政改革步伐,董仲舒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他将前代关于世界秩序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整合,并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提出建立起一个完全按照古代皇帝意志运行的大型帝国机制,以此来确保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这一点直接影响到了后续几百年的中国政治制度设想。
董仲舒倡导的是一种基于直觉理解的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互动模式,他坚信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人们了解自然界如何运作,以及他们自己应该如何生活。他的目的之一是在中国历史中确立儒家作为唯一正确宗教信仰体系,同时还要巩固中央集权政府,使得所有公民服从皇帝命令。这要求人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以及他们应当遵循某些普遍规律——这些规律被称作‘王’字,这个字代表着最高领导者的职位,它象征着连接各个不同领域的人们,最终实现大规模联合的一个中心点。

宋明理学则更加深入地探索这个问题,他们试图找到一个更为精确定义的一个元件或者中心,让它成为解释世界功能的一个基础单元。在程朱理学中,被称为"理"的地方,是被视作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一种抽象形式,它既包括物理世界,也包含精神活动,但同时又超越它们两者。陆王理学则更加侧重于个人内心活动,将它视作产生知识行动能力的心灵核心。
最后,在王守仁的心学体系里,这个核心变得更加清晰简单,而且具体化。一方面,他否认任何外部因素对思考过程可能产生影响,只承认内部结构决定意识内容另一方面,对待这些结构自身也有严格要求,所以他最终推崇一种绝对自足式思考模式,即使对于复杂多样的情况也如此处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在心理层面还是在社会政治层面,都试图寻找那些能够表达最基本真实状态的事项或情境,从而构建起这样一种观点:无论何时、何处,无论哪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声音,那声音就是每个人内在深处那个没有偏差,没有错误,没有分歧的情感反应,每个人都是通过这一途径联系到的其他所有人的感觉器官及思维过程。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保持这种联系,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完美无缺、一致无违的小组合作单位,或许甚至整个地球上所有生物都会因为这种联系而感到紧密相连。这意味着尽管不同的环境条件及不同时间段里的生活方式造成差异,但是至少对于那些真正关注内省并努力理解自己实际经验的人来说,他们总会发现某种东西-特别是一些非常基本但很重要的事情-始终不断回归回来,当你做好准备接收它们的时候,你会惊讶发现你的需求恰恰符合它们提供给你的解决方案,因此虽然很多事情似乎分散开去了,但是其实它们仍然紧密相连,而且正在等待你去发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