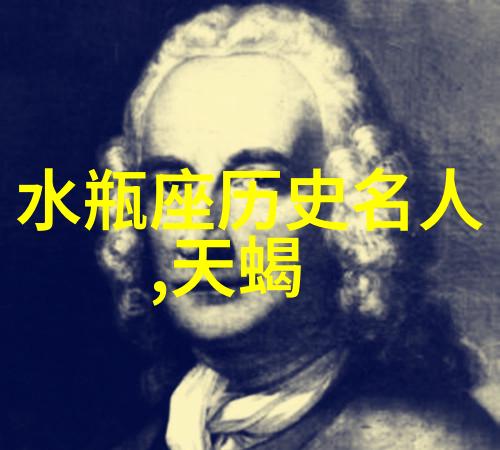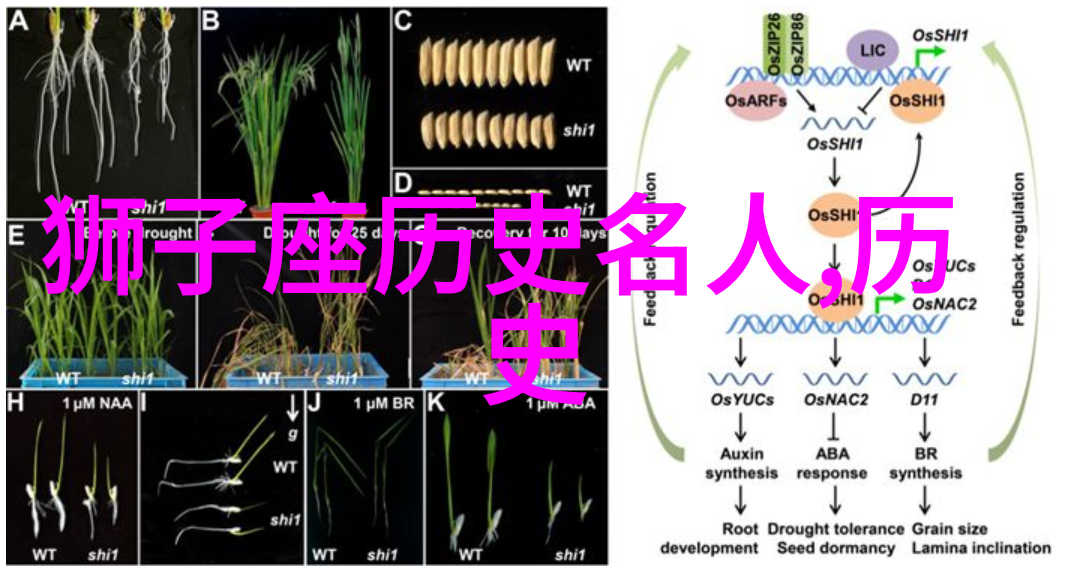燕昭王深信乐毅为知己,乐毅则真诚地致力于回报他。然而,燕国大夫骑劫心怀不轨,他既擅长武艺又精通兵法,却无法超越乐毅的位置。因此,他便伺机图谋掌握军权。

骑劫与太子乐资关系密切,便向后者提出了自己的疑惑:“齐王已逝,齐国仅剩莒城和即墨两地,其余领土皆在燕军之手。尽管乐毅半年内攻下了七十多座城池,为何却花费数年未能拿下这两座强holds?其中必有隐情。”太子点头称是,但未发言。骑劫继续道:“如果乐毅真心要征服这两个城市,他早就可以轻易完成任务。他怕的是齐国民心不稳,因此采取恩德感化策略。一旦齐国人真正归附他,那么他岂不是能够成为新任齐王?而且他若回到燕国担任臣子,这种结果实在荒唐!”太子将此话告知了燕昭王。
一听此言,燕昭王愤怒得几乎跳起来,用节杖责打太子二十板,并斥责其忘恩负义。他说:“先祖的仇敌是谁让我们得到安宁?昌国君的功绩实在难以衡量。我等对待他如同恩人,又恐不足以表达尊敬,你们还敢诽谤他?即使他真的成为了齐王,也应无可厚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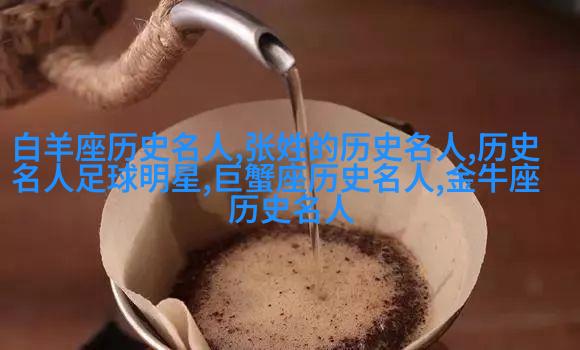
责罚完毕后,燕昭王派使者携带节杖前往临淄,对乐毅表示忠诚,将其立为齐王。但当使者返回时,报告了樂毅坚决拒绝接受封号的情形,不愿背叛他的誓言,而是愿意死也不会接受这一命运。深受感动的燕昭王泪流满面。
然而,这次事件让太子承受了一顿痛打。这件事虽被推到脑后,但终究难以忘怀。在公元前279年(周赧王三十六年、赵惠文 王二十岁),随着燕昭王去世,太子登基成为著名的历史人物——“西施”,也就是后的“开明”或“文化”的标志——二世;而正如曾经信赖过伍员的人物一样,有见识的人会明白,“善始者不必善终”。如此转变,让人们意识到事实上的政治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这个时代里,一些人的忠诚往往因为新的局势变得毫无价值。而他们的心路历程,即使是在千百年的未来,也依然令人感到悲凉和思考深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如何从内部冲突中挣扎出来,同时也体现了个人的忠诚与背叛,以及个人命运如何受到历史潮流影响。这是一个关于英雄、忠贞、权力的故事,它揭示了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勇士来保护自己,从而引导着整个民族走向更好的未来。而对于那些渴望实现梦想的人来说,他们是否能够抵抗住外界压力并保持自我,是一个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