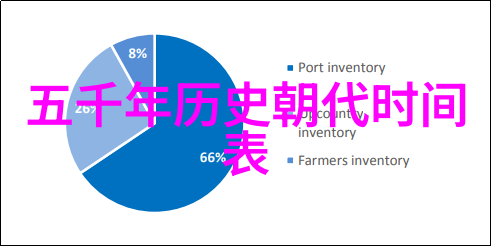文化的影响力。我记得2011年,在那个全球范围内的“占领”浪潮中,我们智利也掀起了一股浪潮。我那时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当智利的卡米拉•巴列霍(Camila Vallejo)站在全球舞台上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者”时,我开始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了兴趣。
智利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样板和典范。自1973年的军事起义以来,我们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最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这使得智利在经济、教育和医疗等领域都进行了私有化。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社会形态,但仍有一些人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了抗议行动。
然而,这不是智利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智利的历史表明,由于智利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智利的大土地所有者保留了强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力。因此,类似于这样的社会运动在智利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虽然我不是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但我知道这些抗议活动是对我们智利历史的一种回应。在智利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我对此有些了解。智利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天主教会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掌握着智利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在这个社会里,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三足鼎立,形成了一个由大土地主、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社会结构。在这个时期,只有富人才能在智利的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工人阶级和底层农民还处于 marginalized(被边缘化)的状态。
智利出口的主要物资是铜矿,因此铜矿工人成为了智利工人运动的主力。在这方面,智利特尼恩特(El Teniente)铜矿工人运动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通过“男性气质”成功地对抗了矿方对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进行的规划和管制。此外,铜矿工人们还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建立起了“英雄化了的”工人运动的传统,并组建了强大的工人社区,为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虽然我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但是我对智利历史上工人运动的发展还是有些了解的。
量,智利党和智利社会党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为智利工人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然而,智利的资本家们对工人运动并不感到欢迎,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们就利用政府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工人运动进行打压。
不幸的是,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智利的党也曾在苏联的指挥下行动。20世纪30年代,尽管智利内部的法西斯倾向比世界其他地区要弱,但智利党仍然与智利社会党、城市小资产阶级政党“激进党”联手,并按照苏联的指令实行“人线”政策。然而,“人线”制定的各项政策并没有真正得到推广和执行,反而受到右翼政党及其背后的社会力量的强烈反弹。只可惜,苏联在二战过程中的让步和委曲求全最终导致智利党和“人线”并不能真正挑战智利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权力基础,更不用说挑战他们的代表即智利右翼和自由主义力量的权威。虽然“人线”和进口替代战略给智利中产阶层带来了好处,但对智利工人来说却几乎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智利工人的强大威胁到了“激进党”,特别是该党右翼的社会基础。而这时,冷战开始了,美国压力下,不再激进的“激进党”开始对智利工人采取压制措施,智利左翼和智利工人阶级猝不及防。我们可以看到,不到30年后,这段历史又几乎重复了一遍。
然而,20世纪50年代,智利当局对工人运动的打压并没有使智利工人退缩,相反,社会冲突加剧,其中智利当局的紧缩政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虽然这一次打压并没有让智利党全军覆没,但他们仍然跟随苏联的指导并放弃了原本的社会主义理念,转而扮演西欧各个社会党的角色。有趣的是,智利社会党比他们的欧洲同僚更加激进,他们的理论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同时他们也对智利工人运动提供了巨大支持。
我所在的政党和智利党相比更加倾向于社会主义,虽然在实际中并没有根本区别。我的同党人阿连德就是出自这个政党。在皮诺切特被推翻后,我党的阿尔梅达派和智利党一样,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支持下向皮诺切特政权发动武装斗争。这个时期,智利右翼转向“现代”右翼,并开始建立右翼群众运动,这和西欧天主教运动以及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策调整一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越来越有力量,挑战着考迪罗和教会结合的统治阶级。这些社会运动获得了苏联和古巴的支持,成为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统治阶级的眼中钉。特别是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采取了各种压制手段,比如支持右翼份子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以及使用间谍和暗杀等手段。对于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我们要格外加强警惕。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这些运动主要采取了直接的手段,比如针对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干涉,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与抗争,尤其是古巴对拉丁美洲社会运动的支持,美国方面开始采取一些改良性质的措施,比如组织所谓的“进步联盟”,并鼓励拉丁美洲统治阶级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包括智利。但是美国和智利统治阶级的期望落空了,弗雷的有限改良措施并没有让智利人民放弃斗争和社会运动,反而激起了更多的要求。然而这些要求并不能在智利现行制度内得到满足。智利社会党的激进派阿连德就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了总统,并且形势愈发紧张。例如,部分底层无房民众无法等待智利政府漫长的处理过程,在大学生、教会、劳工、以及激进运动MIR的支持下,他们于1970年1月采取直接行动占领了圣地亚哥郊区的住房。我们当时建立了一个名为“班德拉”(La Bandera)的社区在农场里生活。在阿连德总统执政得到知识分子们的直接支援,我们的社区成为了活动的温床,建构出了某种“穷人的公共领域”,甚至拥有了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潜力。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尽管智利的局势已经到了临界点,阿连德始终没有跨出最后一步,也是决定性的这一步。于是,我们都知道,在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作为智利统治阶级的代表,在美国方面的全力支援下发动了政变。
之后,皮诺切特政权不仅在所谓“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的支持下,在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了非常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而且在领域也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这些“改革”在智利推翻军政权之后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了。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切断智利社会,尤其是智利社会底层和活动的联系,具体的措施主要有(1)通过严格限制集体谈判,剥夺工人权利; (2)破坏农业协会和农民组织,剥夺农民权利; (3)将社区领袖拘留或杀害,使社区活动无法持续; (4)严厉限制言论自由,宣传对政府的绝对忠诚。这些措施给智利社会及其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直到如今都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通过让雇主在我们工作时可以雇佣代替者,设立一个被称为“谈判团体”(bargaining group)的组织以分化和削弱我们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再加上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工作不安全,智利的工人阶级渐渐失去了通过联合行动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同时,政府通过切断政党与社会基层的联系,并集中财权于中央,强制贫困人口被隔离和设立多个“相互竞争”的代表机构等方式来削弱底层群众的集体力量和行动能力。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也遭受了市场化“改革”的破坏,这些举措让我们底层群众变得更加破碎化和原子化,失去了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智利的资产阶级组织起来,并与政府结合起来。这种情况只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权力,削弱我们群众的反抗。我们并没有真正从市场化“改革”以及相应的措施中获益,甚至许多人认为社会平等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我们并不认同和接受皮诺切特政权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些措施剥夺了我们通过不同途径改善生活的权利。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通过社会运动表达我们的诉求。我们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新老自由主义的历史,更是我们不断抗争的历史。虽然前路漫漫,但我们和世界地区的人民将会一起上下求索。